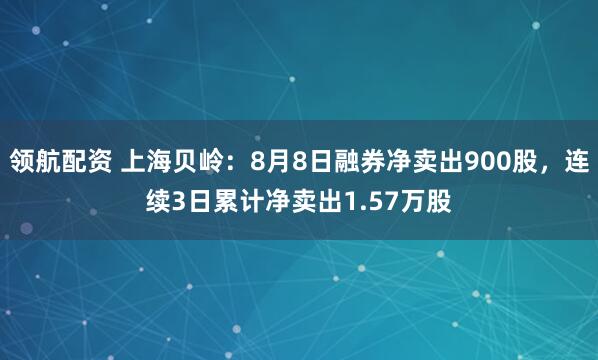抗战时期优选策略,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
在外人看来,这二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但作为在汤恩伯身边多年,熟知内情的吴绍周在其回忆录中却说出了一个让众人没有想到的内情:汤恩伯与蒋鼎文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外人看起来那么大,更多的是二人特意营造出来的让蒋氏放心的假象。
想想也是。
作为以蒋氏嫡系、亲信、学生自居的汤恩伯,又岂会给深受蒋氏信任,特意派到一战区坐镇的蒋鼎文以难堪呢?
让蒋鼎文难堪,其实就是让蒋氏难堪。
这种事情,一贯精明的汤恩伯是不会做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二人之间没有矛盾。
毕竟在一口锅里捞饭吃,勺子与勺子之间,筷子与筷子之间,互相碰撞是常有的事儿。
但这种矛盾,并不是在外人看来那种针锋相对。
这种事情,不是熟悉内情且精明之人是看不破的,而吴绍周恰好就是能看破这一点的人。
汤恩伯其人,乍一看脑袋大脖子粗,一看就像伙夫,但实际上精明得很。
他和蒋鼎文之间暴露在外的那种矛盾,就是特意营造出的让蒋氏放心的假象。
汤恩伯和蒋鼎文都是蒋氏的身边人,对蒋氏的性格以及行事风格应该是再了解不过了。
蒋氏的心理是,他非常希望下面的将领会团结一致,但又不希望他们团结的过于一致。原因也很简单,不团结一致就打不了仗。团结得过于一致,他又害怕无法掌控。
上佳的办法就是既有矛盾,也有合作。只有这样,蒋氏才有可能插手做裁判,这才能让手下那些人即便不想听他招呼,但又不得不听他招呼。
说起来,这就是蒋氏所谓的驭下之术。再简单一点儿说,就是平衡。
可能会有人会说,吴绍周的说法也仅是一家之言罢了,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呢?
那就得说说汤恩伯拉部队的手段和为人处事之道了。
在蒋氏嫡系部队中,在拉部队这方面主要有两种做法,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陈诚式和汤恩伯式。
陈诚式的做法很普遍,也就是说每当陈诚提升1级,那么他就会把紧跟他的部下提升1级,就这样亦步亦趋,一点儿一点儿的把自己的队伍拉起来。如陈诚之于罗卓英。
汤恩伯式的做法是,并不在意以前的部下职位与自己等平,甚至当在自己的部队中没有合适的位置时,他还会把这批人举荐到其他部队去,担任与自己平级的职务。
比如在他担任第89师师长的时候,就保举张雪中和冷欣担任师长,比如在他仍然担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就保举何柱国担任15集团军总司令。
当从自己系统内出去的师长多了,他就可以当军长;当军长的多了,他就可以当集团军总司令;当集团军总司令多了的时候,他就可以担任更高职务。
汤恩伯就是采用这种办法,让部下们把他涌上去。这叫做水涨船高。

汤恩伯式和陈诚式虽然各有利弊,但要从实际控制部队的角度来说,汤恩伯式是不如陈诚式的。
但汤恩伯也没有办法,他是半道进入黄埔系的,既没有参加过东征,也没有参加过北伐,在黄埔生内的影响很小。
在他部下的那些黄埔1期生们,有的资历甚至比他还要高,这就使得汤恩伯无法像陈诚那样亦步亦趋的把部下拉起来。
汤恩伯拉部队的第2个手段就是凡是掌有实权的地方,都用黄埔毕业生。
可名声打出去之后,麻烦事儿同样不少,越来越多的黄埔生投奔到他的旗下。
位置就那么多,人却严重超标,汤恩伯就想了两个办法。
一是优选策略,这批人充作幕僚;二是在部队内增设副师长和副军长职务。
由此,在汤恩伯系统内就出现了这样一幕,若论幕僚和副职的数量,各大派系就没有超过汤恩伯部的。
至于那些杂牌军将领,则逐渐的被边缘化了。例外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吴绍周。
在汤恩伯系统内,杂牌军将领只有吴绍周能够像黄埔系将领们那样循例升迁。这个例外别说别人了,就连吴绍周自己也有些糊涂。
在不了解汤恩伯之前,吴绍周还以为他之所以得到了特殊待遇,是因为在1932年他担任267旅53团团长,参加进攻鄂东黄安红军根据地时,曾经救过陷入重围的汤恩伯,这才让汤恩伯对他另眼看待。
随着对汤恩伯了解的加深,吴绍周才发现,他之所以能在汤恩伯部获得特殊待遇,并非是因为他救过汤恩伯,而是汤恩伯需要在他的系统内树立一个标杆。
按照汤恩伯的话来说,你们不都是说我排除异己吗?吴绍周还不是行武出身?我不是同样保举他不断升迁吗?
因此,吴绍周在汤恩伯系统内往好的方面说是一个榜样,往坏的方面说就是一个样品,一个搪塞其他人抨击汤恩伯排除异己的样品。
不过,吴绍周的运气实在是欠佳。
1948年10月的时候,蒋氏已经批准他出任第4兵團司令官了,保举人是汤恩伯。
可由于汤恩伯和陈诚的关系太差,陈诚就压住命令不放。
可这一切,吴绍周并不知道。
一直到了11月中旬,吴绍周率85军加入淮海战场,部队已经到达蒙城,这份任命才到。
当时吴绍周还以为这是给他一个送命的官儿,在派他到前线作战的时候才任命他为司令官的。
其实不然,如果没有汤恩伯在背后使劲,恐怕他是得不到这个任命的。
如果说在1948年10月,吴绍周就得到命令,那么他也不会率部到淮海战场。因为在任命他为第四兵團司令官的时候,85军军军长职务已经给了110师师长廖运周。
何况,第四兵團司令官也不会在黄维的12兵團里参与指挥。
吴绍周是完全有理由脱离战场的,只要他把任命宣布,把85军交给廖运周,然后就可以离开12兵團。
可吴绍周考虑的很多,他刚率部加入战场就要临阵换将,这是会影响军心的。
因此,他就把这份命令收了起来,准备打完这仗再宣布。
可他再也没能得到机会。
就这样,本应逃脱被俘命运的吴绍周在淮海战场被俘了。

除对出生于黄埔系将领们的任用,汤恩伯对军内上层那些握有实权的人物也是巴结不已。
比如像何应钦、俞济时、钱大钧,还有军需署长陈良,均与他有不错的关系。
中条山之战后,卫立煌被免职,蒋鼎文由10战区司令长官调任1战区司令长官,与汤恩伯有了交集。
按照吴绍周的说法,汤恩伯与蒋鼎文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
理由是,蒋鼎文虽然是蒋氏的“五虎上将”之一,但手中却没有基本部队。
由此可见,蒋鼎文对军权是没有太多野望的。不然,以他的地位和资历,手中有几个军的基本部队那太容易不过了。
手中没有基本部队,那么蒋鼎文在一战区所能依靠的人也仅有汤恩伯了。这也是蒋鼎文不得不与汤恩伯亲近的原因。
蒋鼎文在蒋系将领中是很特殊的一个人。
很多资料上都说蒋鼎文贪财、喜美人儿。此情属实。
蒋鼎文捞钱的手段确实很多,可放眼看蒋系将领,只要手中有权力,又有几个人不捞钱呢?
就以战区司令长官为例,薛岳一手把控了九战区所有的后勤补给,把负责后勤补给的人全部换上了他的亲信,仅有赣北的罗卓英部例外。
再比如以清廉著称的陈诚,家中一堆孩子,每一个孩子都专门配备了一个保姆和一位家教,以他的工资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反观在重庆地位与陈诚相等的军法总监何成浚都穷到什么程度了?连看个牙病都需要攒钱。
再来说蒋鼎文喜欢美人的爱好,这也属实。可却没有那么夸张,这里面更多的是日军的宣传。
比如在豫中会战期间,日本飞机空投的宣传品里有蒋鼎文一手拿纸钞,另一手搂美人的漫画。
可这是敌军的反面宣传,借以污蔑一战区将领,以削弱一战区将士们的斗志,又岂能相信呢?
可有些人就是这样,宁肯相信别的人的宣传,也不肯相信自己人。
蒋鼎文的第2个特点是扶持后进。
比如胡宗南在担任1师副师长期间,因未能当上1师师长,被调任第22师师长的时候心存不满。
还是蒋鼎文耐心做工作说服了他,这才让胡宗南有了自己的基本部队22师,并由此发展起来的。
可胡宗南良心不多,在因年资不够未能担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的时候,反而对兼任总司令的蒋鼎文不满,硬是架空了自己昔日的指路之人。
蒋鼎文是不稀罕与他计较。
要知道,在蒋鼎文的扶持下,就以诸暨为例,就出了百多位将军,生生造出了一个蒋军“将军县”来。
由此可见,蒋鼎文在蒋军内部的能力是很大的,只不过他并不太在意军权罢了。
很多人说,你这个说法不对呀,怎么能说蒋鼎文不爱军权呢?如果他真不爱军权,那为何在到了一战区之后,要拉拢孙桐萱、庞炳勋、李家钰等人来对付汤恩伯呢?
这个问题,吴绍周同样有不同说法。

吴绍周的说法是,与其说是蒋鼎文拉拢孙桐萱、庞炳勋等人对付汤恩伯,还不如说是蒋鼎文团结汤恩伯来对付孙桐萱和庞炳勋。
这个很好理解,蒋鼎文和汤恩伯都是嫡系将领,从来都是嫡系将领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杂牌的,哪有拉拢杂牌来对付嫡系的?这说不通。
因为只有汤恩伯对一些杂牌军施以压力,这批人才会团结在蒋鼎文身边,以寻求支持和保护。
蒋鼎文呢,也同时可以获得这些人的支持,从而在一战区形成合力。
再比如说,在豫中会战前,一战区挖掘的那些壕沟,其实也是蒋鼎文决定的,并不应该把责任都推到汤恩伯身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合谋后的产物。
因为从挖掘壕沟的数量来看,汤恩伯部挖的壕沟很多,蒋鼎文指挥的部队所挖的壕沟也不少。
而这些壕沟之所以在后来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不是壕沟的责任,而是蒋鼎文和汤恩伯指挥上的问题。
当时,蒋鼎文的长官部位于洛阳,汤恩伯的长官部位于叶县,而蒋鼎文以长官之尊经常到叶县来见汤恩伯。
据吴绍周在回忆中说,汤恩伯就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铭三(蒋鼎文字铭三)先生是个老好人”。
当然,被人发了“好人卡”并不是什么好事儿,起码是对被发“好人卡”的人不是那么尊重的,但也谈不上反感。
其实,汤恩伯和蒋鼎文心中都很清楚,蒋鼎文要想在一战区站稳脚跟,他所能依靠的也只有汤恩伯。
而汤恩伯呢,也认为他要想取代蒋鼎文担任一战区司令长官,除了蒋氏发话,那也是没有可能的。
这也就意味着,二人并没有根本性的矛盾,自然也就不会有大的冲突。
因此,外界所描述的蒋鼎文与汤恩伯之间的矛盾有多么多么大,都是不切实际的。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豫中会战失利后,需要给汤恩伯定一个“将帅不和”的罪名吧。

恒汇证券app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